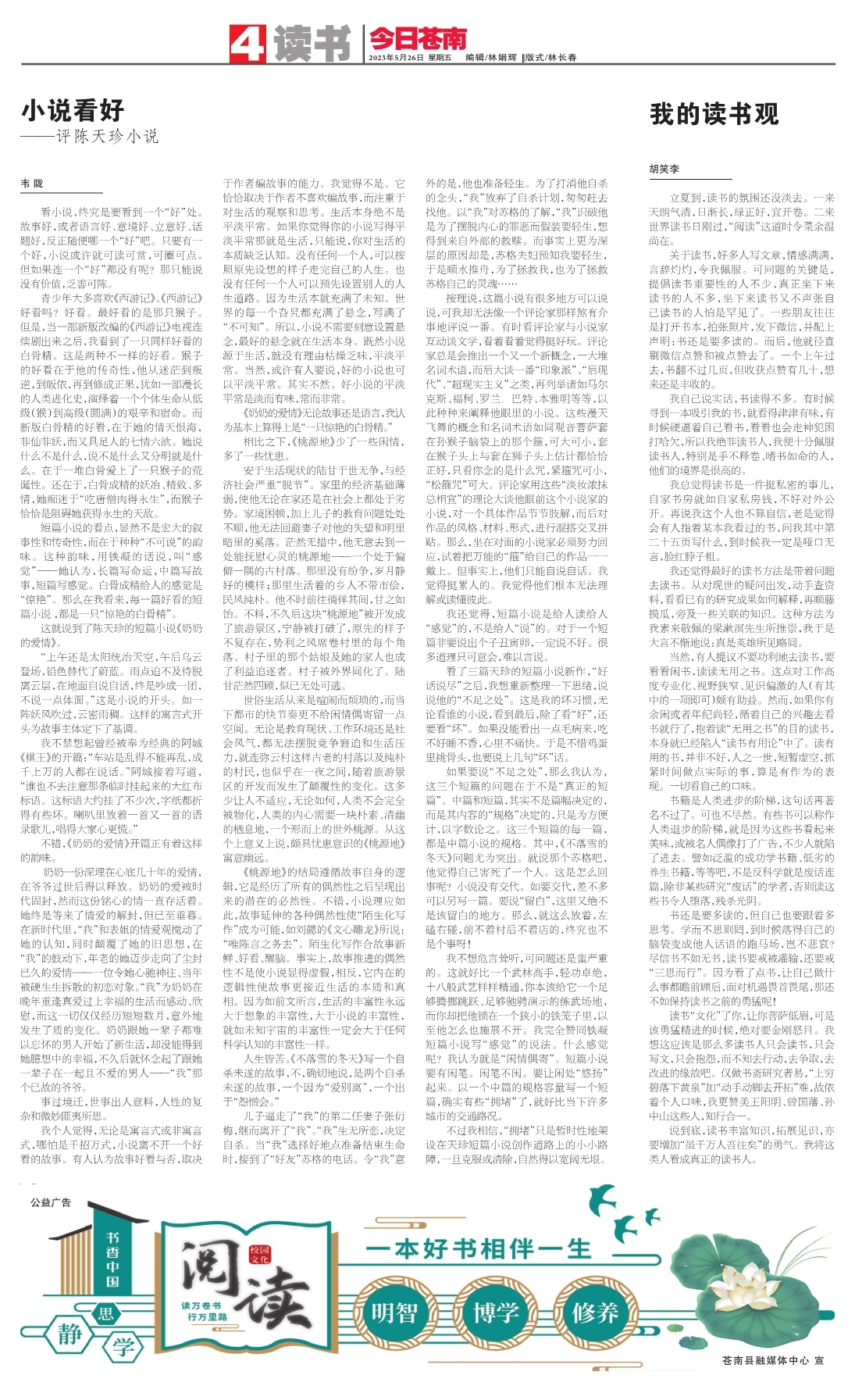

小说看好
——评陈天珍小说
韦陇
看小说,终究是要看到一个“好”处。故事好,或者语言好、意境好、立意好、话题好,反正随便哪一个“好”吧。只要有一个好,小说或许就可读可赏,可圈可点。但如果连一个“好”都没有呢?那只能说没有价值,乏善可陈。
青少年大多喜欢《西游记》。《西游记》好看吗?好看。最好看的是那只猴子。但是,当一部新版改编的《西游记》电视连续剧出来之后,我看到了一只同样好看的白骨精。这是两种不一样的好看。猴子的好看在于他的传奇性,他从迷茫到叛逆,到皈依,再到修成正果,犹如一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演绎着一个个体生命从低级(猴)到高级(圆满)的艰辛和宿命。而新版白骨精的好看,在于她的情天恨海,非仙非妖,而又具足人的七情六欲。她说什么不是什么,说不是什么又分明就是什么。在于一堆白骨爱上了一只猴子的荒诞性。还在于,白骨成精的妖冶、精致、多情,她痴迷于“吃唐僧肉得永生”,而猴子恰恰是阻碍她获得永生的天敌。
短篇小说的看点,显然不是宏大的叙事性和传奇性,而在于种种“不可说”的韵味。这种韵味,用铁凝的话说,叫“感觉”——她认为,长篇写命运,中篇写故事,短篇写感觉。白骨成精给人的感觉是“惊艳”。那么在我看来,每一篇好看的短篇小说,都是一只“惊艳的白骨精”。
这就说到了陈天珍的短篇小说《奶奶的爱情》。
“上午还是太阳统治天空,午后乌云登场,铅色替代了蔚蓝。雨点迫不及待脱离云层,在地面自说自话,终是吵成一团,不说一点体面。”这是小说的开头。如一阵妖风吹过,云密雨稠。这样的寓言式开头为故事主体定下了基调。
我不禁想起曾经被奉为经典的阿城《棋王》的开篇:“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阿城接着写道,“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不错,《奶奶的爱情》开篇正有着这样的韵味。
奶奶一份深埋在心底几十年的爱情,在爷爷过世后得以释放。奶奶的爱被时代固封,然而这份铭心的情一直存活着。她终是等来了情爱的解封,但已至垂暮。在新时代里,“我”和表姐的情爱观搅动了她的认知,同时颠覆了她的旧思想,在“我”的鼓动下,年老的她迈步走向了尘封已久的爱情——一位令她心驰神往、当年被硬生生拆散的初恋对象。“我”为奶奶在晚年重逢真爱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感动、欣慰,而这一切仅仅经历短短数月,意外地发生了质的变化。奶奶跟她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男人开始了新生活,却没能得到她臆想中的幸福,不久后就怀念起了跟她一辈子在一起且不爱的男人——“我”那个已故的爷爷。
事过境迁,世事出人意料,人性的复杂和微妙匪夷所思。
我个人觉得,无论是寓言式或非寓言式,哪怕是千招万式,小说离不开一个好看的故事。有人认为故事好看与否,取决于作者编故事的能力。我觉得不是。它恰恰取决于作者不喜欢编故事,而注重于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生活本身绝不是平淡平常。如果你觉得你的小说写得平淡平常那就是生活,只能说,你对生活的本质缺乏认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按照原先设想的样子走完自己的人生。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预先设置别人的人生道路。因为生活本就充满了未知。世界的每一个旮旯都充满了悬念,写满了“不可知”。所以,小说不需要刻意设置悬念,最好的悬念就在生活本身。既然小说源于生活,就没有理由枯燥乏味,平淡平常。当然,或许有人要说,好的小说也可以平淡平常。其实不然。好小说的平淡平常是淡而有味,常而非常。
《奶奶的爱情》无论故事还是语言,我认为基本上算得上是“一只惊艳的白骨精。”
相比之下,《桃源地》少了一些闲情,多了一些忧患。
安于生活现状的陆甘于世无争,与经济社会严重“脱节”。家里的经济基础薄弱,使他无论在家还是在社会上都处于劣势。家境困顿,加上儿子的教育问题处处不顺,他无法回避妻子对他的失望和明里暗里的奚落。茫然无措中,他无意去到一处能抚慰心灵的桃源地——一个处于偏僻一隅的古村落。那里没有纷争,岁月静好的模样;那里生活着的乡人不带市侩,民风纯朴。他不时前往徜徉其间,甘之如饴。不料,不久后这块“桃源地”被开发成了旅游景区,宁静被打破了,原先的样子不复存在,势利之风席卷村里的每个角落。村子里的那个姑娘及她的家人也成了利益追逐者。村子被外界同化了。陆甘茫然四顾,似已无处可逃。
世俗生活从来是喧闹而烦琐的,而当下都市的快节奏更不给闲情偶寄留一点空间。无论是教育现状、工作环境还是社会风气,都无法摆脱竞争窘迫和生活压力,就连弥云村这样古老的村落以及纯朴的村民,也似乎在一夜之间,随着旅游景区的开发而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多少让人不适应,无论如何,人类不会完全被物化,人类的内心需要一块朴素、清幽的栖息地,一个形而上的世外桃源。从这个上意义上说,颇具忧患意识的《桃源地》寓意幽远。
《桃源地》的结局遵循故事自身的逻辑,它是经历了所有的偶然性之后呈现出来的潜在的必然性。不错,小说理应如此,故事延伸的各种偶然性使“陌生化写作”成为可能,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所说:“唯陈言之务去”。陌生化写作合故事新鲜、好看、醒脑。事实上,故事推进的偶然性不是使小说显得虚假,相反,它内在的逻辑性使故事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和真相。因为如前文所言,生活的丰富性永远大于想象的丰富性,大于小说的丰富性,就如未知宇宙的丰富性一定会大于任何科学认知的丰富性一样。
人生皆苦。《不落雪的冬天》写一个自杀未遂的故事,不,确切地说,是两个自杀未遂的故事,一个因为“爱别离”,一个出于“怨憎会。”
儿子逼走了“我”的第二任妻子张衍梅,继而离开了“我”。“我”生无所恋,决定自杀。当“我”选择好地点准备结束生命时,接到了“好友”苏格的电话。令“我”意外的是,他也准备轻生。为了打消他自杀的念头,“我”放弃了自杀计划,匆匆赶去找他。以“我”对苏格的了解,“我”识破他是为了摆脱内心的罪恶而假装要轻生,想得到来自外部的救赎。而事实上更为深层的原因却是,苏格夫妇预知我要轻生,于是顺水推舟,为了拯救我,也为了拯救苏格自己的灵魂……
按理说,这篇小说有很多地方可以说说,可我却无法像一个评论家那样煞有介事地评说一番。有时看评论家与小说家互动谈文学,看着看着觉得挺好玩。评论家总是会推出一个又一个新概念,一大堆名词术语,而后大谈一番“印象派”、“后现代”、“超现实主义”之类,再列举诸如马尔克斯、福柯、罗兰﹒巴特、本雅明等等,以此种种来阐释他眼里的小说。这些漫天飞舞的概念和名词术语如同观音菩萨套在孙猴子脑袋上的那个箍,可大可小,套在猴子头上与套在狮子头上估计都恰恰正好,只看你念的是什么咒,紧箍咒可小,“松箍咒”可大。评论家用这些“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理论大谈他眼前这个小说家的小说,对一个具体作品节节肢解,而后对作品的风格、材料、形式,进行混搭交叉拼贴。那么,坐在对面的小说家必须努力回应,试着把万能的“箍”给自己的作品一一戴上。但事实上,他们只能自说自话。我觉得挺累人的。我觉得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或读懂彼此。
我还觉得,短篇小说是给人读给人“感觉”的,不是给人“说”的。对于一个短篇非要说出个子丑寅卵,一定说不好。很多道理只可意会,难以言说。
看了三篇天珍的短篇小说新作,“好话说尽”之后,我想重新整理一下思绪,说说他的“不足之处”。这是我的坏习惯,无论看谁的小说,看到最后,除了看“好”,还要看“坏”。如果没能看出一点毛病来,吃不好睡不香,心里不痛快。于是不惜鸡蛋里挑骨头,也要说上几句“坏”话。
如果要说“不足之处”,那么我认为,这三个短篇的问题在于不是“真正的短篇”。中篇和短篇,其实不是篇幅决定的,而是其内容的“规格”决定的,只是为方便计,以字数论之。这三个短篇的每一篇,都是中篇小说的规格。其中,《不落雪的冬天》问题尤为突出。就说那个苏格吧,他觉得自己害死了一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小说没有交代。如要交代,差不多可以另写一篇。要说“留白”,这里又绝不是该留白的地方。那么,就这么放着,左磕右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终究也不是个事呀!
我不想危言耸听,可问题还是蛮严重的。这就好比一个武林高手,轻功卓绝,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你本该给它一个足够腾挪跳跃、足够驰骋演示的练武场地,而你却把他锁在一个狭小的铁笼子里,以至他怎么也施展不开。我完全赞同铁凝短篇小说写“感觉”的说法。什么感觉呢?我认为就是“闲情偶寄”。短篇小说要有闲笔。闲笔不闲。要让闲处“悠扬”起来。以一个中篇的规格容量写一个短篇,确实有些“拥堵”了,就好比当下许多城市的交通路况。
不过我相信,“拥堵”只是暂时性地架设在天珍短篇小说创作道路上的小小路障,一旦克服或清除,自然得以宽阔无垠。
江苏路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仅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文字、图片、视频版权归属发布媒体

